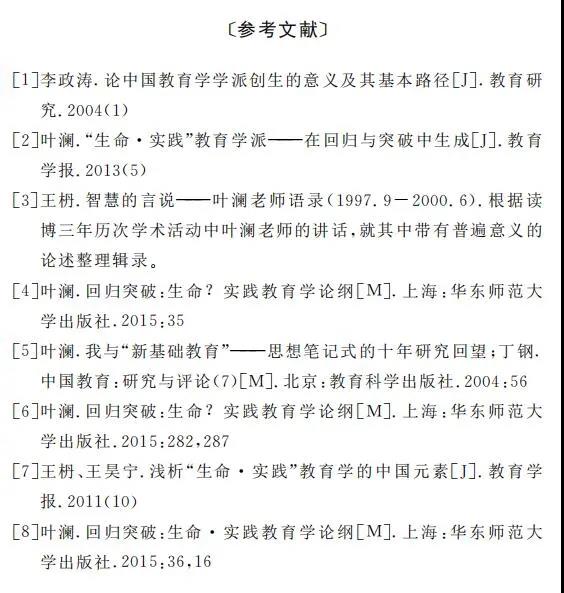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学校转型性变革实践研究为基石,以理论与实践双向构建为特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为目标而创建的教育学派。自1994年起,团队在创始人叶澜教授与学派成员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校变革的“中国经验”。团队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唯一来自教育学的教师研究团队。
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派发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公众号开辟“学派理论建设之路”专栏,将陆续推送“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学者的相关论文,以飨读者。本期为读者呈现的是王枬教授《“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回归与突破》一文,该文以对“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系统性理论建构的分析,阐明了学派回归与突破的学术追求。
本文原载于《教育科学》2015年第3期
全文共 6981 字
预计阅读时间 10 分钟
作者简介
王枬,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副院长。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回归与突破
王 枬
一个学派的产生以至形成,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人物的代表性和群体性;其二,立场的一致性和传承性;其三,学说的独立性和发展性。“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已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意向产生到形态初显,再到逐渐成形和共通互化,经历了孕育期、初创期、发展期、成形期、通化期五个阶段。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三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的诞生,意味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已经开始了自觉系统的理论建构,并进入到理论与实践互为融合的“通化”期,实现了“回归与突破”这一学派的追求。这种回归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研究者自身以及学派群体对已形成的学术自我的超越
回归体现在对学术自我状态的自明,突破体现在对自身学术观念系统的更新。叶澜老师一直强调“学术自我”,并以自身的示范让我们明白了何为学术自我。记得在1998年元旦的学术例会上,叶澜老师在“我的学术自我”的主题报告中就十分动情地说到:
“人生是生命的流程,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活动书写的一本书。而生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原初的唯一的财富,是个体的不断的时空变化,是从‘空’到‘有’的过程。一个常态的人生都是职业的人生。职业活动是生命活动中具有规定性的、具有创造价值的活动。我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是我的职业中的重要构成,是生命中创造价值的活动。这样,我选择的职业与我的人生就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高相关:追求高质量的职业生活和高质量的人生。”
“35年的教师生涯使我对教师职业有了更深的体悟。在教师职业中,我又选择了研究作为自己职业的基础,有意义的教学应该如此:只有在研究中,教师才会感到快乐;以研究为主的生涯在本质上才是学术生涯。而在研究中,出于对人文学科的偏好,我又以教育与人生关系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主线和主题。”
“学术研究提高了我把握自己人生的自觉性,使我越来越清晰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应是社会奉献与个人满足统一的人生。学术研究促进了我的精神成长,帮助我去思考‘我是谁’,我在哪一个领域对社会的贡献最大,我该怎样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学术研究充实了我的生命,使我学会了选择。在我看来,教育是一个使自己和人类都更美好的事业,因而,对教育的选择就是对幸福人生的选择。我的事业、我的生命就体现在我对教育的自觉选择上。”
“将自己对生命的体悟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抽象,这就是我学术研究的土壤。写文章是生命的迸涌,而不是简单的思维记录。”
“我热爱我所从事的职业,我热爱自己所进行的研究。这也是我的人生态度:喜欢发现,喜欢创造。”叶澜老师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她不断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丰富、充实、更新,从20世纪80年代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老三论”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对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所谓“新三论”的关注,再到21世纪初对复杂理论的思考,无不体现了她对新兴科学的敏感和学习;从研读《黄帝内经》到关注“脑科学”,再到请教“表观遗传学”的基因概念,更是展现了她更替内在知识的自觉。《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出的155本著作也为我们呈现了叶澜老师在写作这本论纲时的阅读地图。她不仅身体力行,也对学生及团队成员不断提出突破旧我、严谨学风的要求。
“没有研究者自我的突破,难有内生长意义上的学术更新与创造。”
在研究中不断超越学术自我,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继而获得自我发展,从而具有新的影响他人发展的教育力量,并在研究的积淀和成果中体现出独特的教育学之生命实践气质。这正是学派创建及发展的前提。
二、研究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及建设中国教育学派的自觉
回归体现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给予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的深度认识;突破体现在对建设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且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教育学的追求。
叶澜老师主张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内蕴着丰富的教育精神与智慧。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滋养了中国教育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教育使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扬。如中国文化传统在价值取向上,指向人的自强与自立,关怀人间生存与世道的完善,且把“天人合一”看作最高层次上的统一。这应成为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基本立场。又如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之独特性集中表现为:整体综合、弥漫渗透;对成同根、相互转化;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等方面。这应成为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唯有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家园,才能将中国近代教育学因为“引进”而断裂的学术命脉重新连接起来,使中国当代教育学在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下根深叶茂,日益壮大,彻底摆脱被其他学科、其他国家教育学“双重殖民”的状况。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中国当代教育学人的学术尊严。
叶澜老师认为:教育学在新时期发展的方向不应再是追随西方,“唯洋是瞻”,以西方为标准或前提进行的“中国化”,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原创的教育学。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具有浓郁的中国立场、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这里的“中国”,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从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己的学术之根,也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以中国当代的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作为教育理论的生长之源,而且指中国的教育学者应当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声音,为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世界性的贡献。这里的“原创”,不只是指教育学的研究要获取中国自己的原始素材,也不只是指教育学的研究要有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而且指中国的教育学研究应当基于本国教育发展的需要,研究本国的教育问题,进而得出在本国或全球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一认识,叶澜老师以“生命·实践”这两大核心要素为基点,力求以深深扎根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土壤的原创研究,去推动真正体现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建立。
“我们想通过‘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这声音将揭示平凡教育事业蕴涵的丰富与伟大;蕴涵的与人类最基础的存在———生命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蕴涵的对创造、智慧和发展的呼唤;蕴涵的对健康人性、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价值……而我们的学术生命,也将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走出昨天,走向明天,快乐而艰难地行进在已经踩出的小道上。”
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努力证明:在教育学的当代重建中,教育学人的发展,包括信心、勇气、智慧及其对教育改革的投入,是谁也不能代替的重要力量。
三、研究者自身以及学派群体教育学观的厘清及教育观的重构
回归体现在重新思考教育学及教育的一些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并厘清属于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突破体现在基于返本开新的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教育学。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教育学为己任,这暗含着以确认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为前提性判断。所谓“独立学科”的标志,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方向”,取得与其他学科平等交流的资格。叶澜老师概括了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五个特点,即:从依附到独立、从单一到多元、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封闭到开放、从异乡到本土,由此特别强调了教育学的内立场的重要,并指出: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学正处在各类学科的交汇点上,因而,教育学不仅能从不同学科汲取资源,而且完全有可能因对教育的深度研究,达到对人类有关自身、社会和活动的认识,作出教育学意义的贡献。这不仅是教育学人的历史使命,更是当代教育学人的社会责任。
建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必须厘清教育学观。叶澜老师以“教育存在说”构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观,这是一个具有内发展、内生长机制的,能够生存发展的有机系统。又以“复杂/综合性”界定了教育学作为“事理学”的学科性质为“育人的社会学科”,其中包含了科学、艺术与技术。再以“复杂性理论”指出了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对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教育活动的直接对象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故而,与复杂研究的方法论更具适切性。”
建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还必须重构教育观。首先,叶澜老师对教育的概念做出了多层界定。第一层次为划界式界定: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第二层次为结构性界定:教育活动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教者与学者、教育内容和教育物质。第三层次为功能性界定:教育是具有直接影响个体多方面发展的内功能和间接影响社会多方面发展的外功能的独特社会活动。其次,叶澜老师分析了教育存在的依据,阐述了“生命·实践”的深刻内涵。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和人类这一“类生命”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教育存在的依据,也规定了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固有职能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职能。“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这一称谓则标示出学派关于教育学的理论是以“生命·实践”的核心要素为特征的。这不仅是学派建设的立场,也是学派理论的基因,还是学派思想的命脉。
在此基础上,叶澜老师以“教天地人事 育生命自觉”做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是什么”的中国式表达。
“‘天地人事’是‘教’所要传递的文化内容,是外在已有的‘类知识’……‘教’的任务,就是使个体接受这些外在的类认识,并能为其个人的生存发展所用。而‘生命自觉’则指教育对于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培育生命之自觉,这是人的精神力量的内在成长,是‘育’的任务和指向。……教与育之间在实践中只有合为一体,才能达到立人的目的。”
“由教‘天地人事’而达‘生命自觉’之育,是一个涵蕴、转化的过程。所谓‘涵蕴’是指‘生命自觉’之育内在于‘天地人事’之教的过程中,教与育不是两件分开的事项,尤其是‘天地人事’中,人与事的内容本身就直接阐述着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之道,直接在人的生命实践过程中,而‘人事’又是中国教育内容的主要构成。故双方的关系是外与内的关系,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累积、化成。所谓‘转化’,一是指外在的类文化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人格;二是指外在的师之教转化为弟子内在的精神世界之充盈,直至生命自觉之形成。”
“生命·实践”教育学主张把基于中国教育发展需要、研究中国教育问题,进而得出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渗透于教育学科,把对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浸润于教育学人的个体生命,这便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者深度介入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实践
回归体现在以实地介入式的研究扎入当代教育实践涌动不息的大海,进入到学校日常而平凡的教育实践活动之中;突破体现在通过研究推动学校的深入变革,并在变革的实践中逐渐生成“生命·实践”教育学。
叶澜老师一直强调要深入实践,这种实践是有意识、有对象、有目的指向和行为策划并付之实施的自觉活动。1994年由叶澜老师领衔开始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就是“实地介入式”的“研究性变革实践”。这是在中国学校教育大地上的扎根式研究,是区别于传统教育学的另一种学术研究和书写方式。“新基础教育”中“新”的解释也在实践的推动下经过了几次升华。1994年的探索期,“新”被界定为理论上要对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并形成新的体系,实践上要构建符合时代需要并服务于新世纪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校实践模式。1998年即将进入发展期,“新”又被解释为重点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和培养模式三方面上更新,并初步构建了以观念形态、学校实践形态和师生存在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变革。2004年的成型期,“新”又以未来性、生命性、社会性、主动性、潜在性、差异性、双边共时性、灵活结构性、动态生成性、综合渗透性等十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新基础教育”体系。总之,“新基础教育”从未停止过变革和更新。正是这种从设计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生命自觉,使“新基础教育”呈现出一种积极而富有生气的生命状态。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在对20年来“新基础教育”实验成果总结、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既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及教育发展需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教育学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与“新基础教育”实验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一方面,“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立在“新基础教育”长期实验的基础之上,具有扎实丰厚的实践根基;另一方面,“新基础教育”实验也在“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中得到了升华。
“‘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
“它是中国的,它是当代的,它是教育学的,它是在研究实践中创生的,它是团队的,它是有魂、有体、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它是整体、具有生命态、内聚着生命能量的,它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大家庭中有自己个性和独特成长方式的‘新生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严肃而深邃的著作中,叶澜老师有许多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既体现了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敏感,也表明了她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洞察。如以“冬虫夏草”表明教育在转化人、
发展人方面所起的作用;以“果蝇”比喻介入式研究在每天都在进行的学校日常教育实践活动中感受教育学内立场的存在;以“剥洋葱”比喻现象、本质之无区别;以“一地鸡毛”来说明如果缺乏把握事物构成的基本认识框架,就可能只看到每一片鸡毛的独特,却不能透过这一地鸡毛看到鲜蹦活跳的鸡;以“基因”比喻教育之根并作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核心概念……这样的话语方式,带着研究者的生命温度,表现了来自实践又连接生命的教育学的“草根情结”,展示了发展教育学的学术智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