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构背景下,面对骨干教师“新老交替”所致的教师队伍变化,以及骨干教师迭代赓续的需要,如何提升教研质量,推动新骨干的培养,是教育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第五辑)》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集中讨论了相关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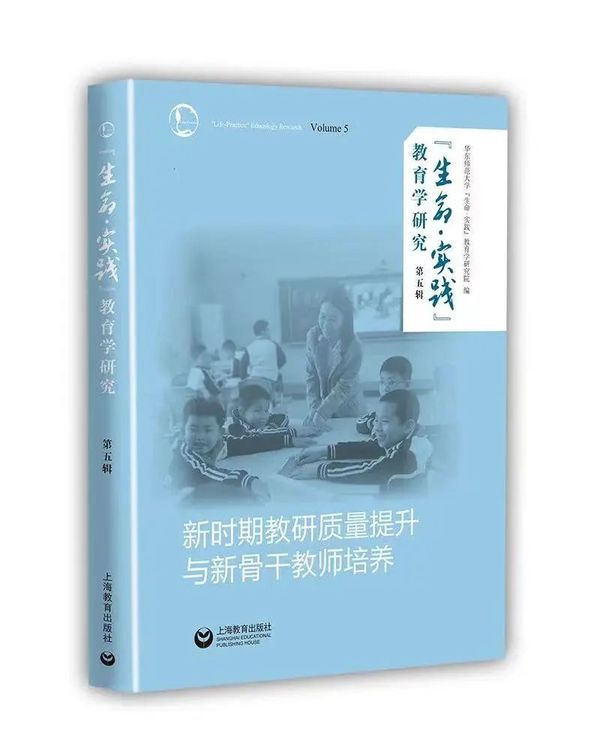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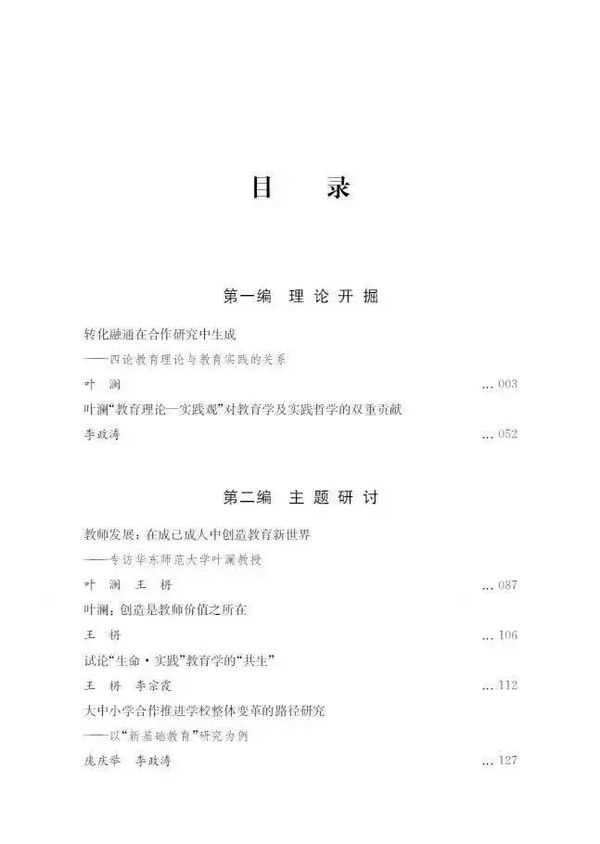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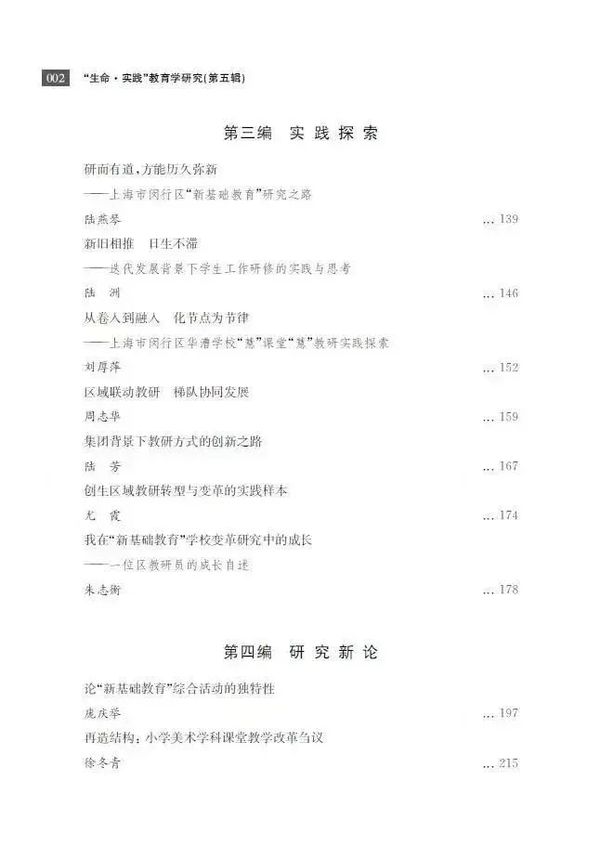

本书通过对叶澜“教育理论-实践观”的理论开掘,帮助读者读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增进建构新型转化融通关系的探究自觉;
通过对叶澜教师观的主题研讨,帮助读者读懂教师,提升教师转型发展的自觉;
通过对骨干教师发展策略的实践探索,从区域层面、集团校层面、学校层面、学科层面、个体层面等不同责任主体角度呈现骨干教师发展的独特经验;
通过一系列研究新论,进一步从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的具体领域进行丰富与拓展。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致力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它传承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优良传统,围绕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研究方法论和教育学反思与重建等四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本书名誉主编为叶澜教授,主编为李政涛教授,执行主编为张永教授。
精彩书摘
叶澜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深层问题。本文从一般到特殊再到具体三个层面,论述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如何实现转化融通。首先,在哲学层面,本文对影响我国教育学界较深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做了深入分析和选择性判断,澄清了理论与实践的要义、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其次,本文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在教育研究中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教育是什么”的底线式认识,强调了教育复杂事理研究的特殊性,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自身发展变化对推进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性。最后,本人以总主持并持续亲历20余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为例,阐明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在合作研究中实现转化融通、交互生成,概括了理论、实践“魂体相融”的关系表现及其建成。
自21世纪初至今,教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我思考和研究实践中探索的深层问题,也是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2001年、2009年、2014年,本人先后发表了三篇相关主题的论文。2019年年底,我全部解除了自1994年启动的“中国转型期学校整体转型”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主持人和实际参与者的责任。在已过去的20余年中,就该研究,本人曾发表大量文章并出版专著,但尚未就研究中贯穿始终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发生的真实转化、融通与生成,做过专题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在一定意义上了却了这一心愿。本人在亲历基础上,就这一主题进一步学习,系统梳理,以相对完整的方式表达自己目前的认识,旨在与同仁交流并推进相关研究。
全文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欧洲哲学史意义上,对理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再认识;二是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三是以“新基础教育”研究为例,阐述合作研究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融通和交互生成。
一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理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词和话题。但就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个体而言,却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中国自近代以来,学界对这一主题的阐述,主要以欧洲西方哲学研究为基础,教育学界也不例外。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西方哲学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却有很大差异。在此以历史演化为线索,就对我国教育学界有较大影响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做一概要述评,并阐明我们的理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词和话题。但就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个体而言,却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中国自近代以来,学界对这一主题的阐述,主要以欧洲西方哲学研究为基础,教育学界也不例外。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西方哲学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却有很大差异。在此以历史演化为线索,就对我国教育学界有较大影响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做一概要述评,并阐明我们的认识与选择。
(一)传统经典观:亚里士多德人类知识分类的奠基作用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最早从哲学的意义上,明确将人类知识分为理论、实践和技术三大类,并确认理论知识处于最高级、实践次之、技术为末的排序。其评判依据,一在于研究对象的独立和永恒程度,二在于知识的理性思维含量。
理论知识是纯理性思维的产物,故品位最高,可称为“纯粹智慧”。
实践是在理性基础上涉及伦理和政治的知识。在狭义上指以至善为目的之幸福的实现,及其成善之德性养成的伦理活动。在广义上指各行各业相关的人类实践。“合乎正确原理而行动”即为实践,这里的“原理”是指属人的哲学,它包含着人对完满幸福的一种思辨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者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自己是什么人或自己在做什么;对什么人和为什么事情而行动;关于什么和在于什么;有时候还要追问使用什么(如工具),为了什么(如救人),以什么方式(如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实践者还应“对行为的环境和条件逐一认知”。实践需要策划,策划是“树立一个目的之后,去探求怎样和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具有这样品质的实践是“明智”的实践。总之,在实践成事方面,“理论与实践都为必要,但重要的还是经验”。
明智,也称为“实践智慧”。它不同于纯粹智慧的品质,前者在于成事,后者在于至真。
技术是实用性的知识,虽也有理性支撑,但主要由创制的需要而生。它被称为“技术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三大知识分类和三大智慧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在知识论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经典分野和内在联系。
理论的特点是指向确定和永恒的真,即对确定性真理的追求,用的是理性思辨的方法。它超然于现实的物之上,称为“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
理论除了处于知识巅峰地位外,也成为实践和技术必要的、对其有统摄作用的构成因素。为了保证思辨的可靠性,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形式逻辑。哲学理论在价值意义上的另一特征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哲学”“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显然,哲学作为最高的学问,是与当时贵族阶层的生存状态相匹配的。但是,这道出了今天我们的学术还在追求的“人本自由”“为学术而学术”的超然目标,被作为解放了的学术人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的定性直到近代依然保持其传统和尊严,使哲学成为越来越远离人间烟火的独立王国。
与人间烟火紧密相关的是实践。实践一方面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生活和社会伦理规范,另一方面,更广意义上的实践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务。
“实践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是处理事务的理性智慧,所形成的是事理。但因影响事务的因素之多样、变化和不确定性,所以它只能是第二等知识。
亚里士多德无法用确定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是事理,也尚未发展出研究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故只是用列出哪些因素和能力是处理事务所必须顾及的方面来说明事理。也许,这些因素一般学者也能想到,显得有些稀松平常,且哲学家们大多不涉人间杂务,以至近代哲学中关注、理解、阐述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和实践智慧者,偏重取其狭义规定,既成传统。这种取向在康德(I. Kant)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与提升。
在区分理论与实践两类知识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于提出:理论与实践两类不同性质的知识,应有不同的研究路径、不同的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这一重要的学科区分的方法论判断,依据就在研究对象性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物的自然科学、研究人事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学科空间的“四分架构”,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中,已有了慎思形成的初步架构。如此格局,虽历经变化,但事实上至今还存在于学术世界。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与转型
笛卡尔与康德……
